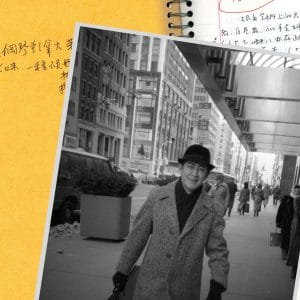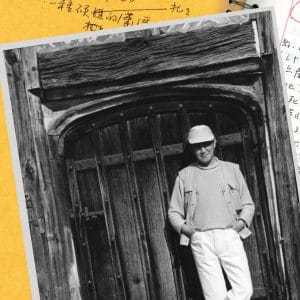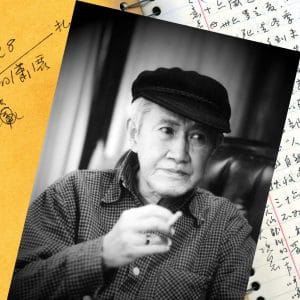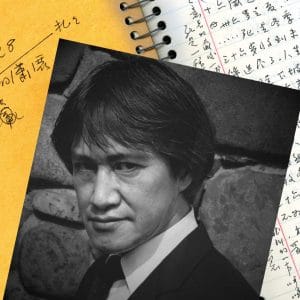第四十二講:《十九世紀英國文學》(四)
木心於本文續談十九世紀文學批評,介紹托馬斯·卡萊爾(Thomas Carlyle)、約翰·羅斯金(John Ruskin)及沃爾特·佩特(Walter Pater)等著名批評家,分享他對這些批評家的看法。
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
批評是很廣義的名詞。講文學史,當然是文學批評。就文學本題講,所謂文學批評,是指散文。歷史學家,善批評者,作品收入散文。
托馬斯·卡萊爾(Thomas Carlyle,1795-1881)。大名鼎鼎。十九世紀後半的大批評家。我讀羅曼·羅蘭和愛默生時,起勁地讀過一陣卡萊爾。我告別羅蘭時,也告別卡萊爾。讀書如交友。讀萬卷書,朋友總有千把個,但刎頸之交,不過十來人。卡萊爾不算。
父為石匠。農家子弟。求學於愛丁堡大學。當時學而優則教(士),他不想去當教士,最終決定堅持信仰,靠講課、寫作維持生活。長壽,身體卻壞,一輩子胃病。
1825年出《席勒傳》(The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)。1826年結婚,此後撰稿為生,所作大多為德國文學論文。1837年,出版重頭書《法國革命》(The French Revolution: A History)。1841年,將多次講演成集《英雄和英雄崇拜》(Heroes and Hero Worship)——他的名字與此著作聯在一起。後又出版另一代表性著作《過去與現在》(Past and Present)。
怎樣評價卡萊爾?
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,長得雄偉,愛默生推崇備至,敬愛他。我少年時,家中陰沉,讀到卡萊爾句:
沒有長夜痛哭過的人,不足語人生。
大感動。又有:「打開窗戶吧,讓我們透一口氣!」(呼吸英雄的氣味)但這種偉大崇高的靈智境界,進去容易,出來很難。一進去,年輕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。藝術家不能這樣憑著英雄氣息成長的。一個人要成熟、成長、成功,其過程應該是不自覺、半自覺、自覺這樣一個自然的過程。
羅蘭、卡萊爾對我的不良影響(不是他們不良,是於我不良),是因為他們一上來就給我一個大的自覺,一個太高的調門。
人要從凡人做起,也要學會做觀眾。
羅蘭一上來就起點太高,結果並不長進。他在師范大學時寫信給托爾斯泰,是這點水準,到老得諾貝爾獎,還是這點水準。傅雷也相似,上來就給羅曼·羅蘭寫信,從法國留學回來,到紅衛兵衝擊,還在那些觀點。
起點高,而不退到觀眾席,老在台上演戲,那糟糕極了。後來羅蘭訪蘇,簡直失態。
他是講文以載道的。
卡萊爾在文學上比羅蘭好,辭藻豐富,句法奇拔。他認為無情與冷漠是世上的大罪。他反對一切民主主義,要有英雄偉人出來領導——對的。可是英雄呢?偉人呢?
我以為是不得已,才找個民主制度。民主是個下策。再下策呢?一策也策——明乎此,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。
其他策,更糟,所以乃為上策。
所謂民主,是得過且過的意思。一船,無船主,大家吵,吵到少數服從多數——民主。
民主是不景氣的、無可奈何的制度。卡萊爾痛恨快速發展的商業工業社會。眼光遠。他反對物質主義。
我與他不同的是,他演講,講正經話,我只能講俏皮話,笑話,罵人,寫散文詩——骨子裏,倒是英雄崇拜。
我反對民主?這話要有一個前提的。要這樣講下來,把民主和英雄主義對比下來,才可以講講。
「歷史是更偉大的聖經。」這話也是他說的。說得好!
我們講文學史,是在講文學的聖經。我們學文學,就是文學的神學。
別說我反民主——別誤解。目前,民主是唯一的辦法。我希望今後東歐、中國有了真的民主,
要是現在現成的美國式的民主。拿一個更好的民主出來,這樣子,七十年受的苦沒有白受。
不能把西方這種暴力、性、刺青……拿來。
約翰·羅斯金(John Ruskin,1819-1900)。生於倫敦,蘇格蘭人,父為酒商。童年少年很快樂。1839年在牛津大學以詩得獎,四年後發表《近代畫家》(Modern Painters),1849年發表《建築的七盞燈》(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),1853年發表《威尼斯之石》(The Stones of Venice),均屬藝術論文集。
他談藝術,談談就談到當時的社會道德,這是他關心的東西。他在倫敦大學講藝術,都宣傳社會道德、人生等等,也是文以載道派。他的目的,想創造純潔、快樂的理想國。
「美學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。」他說。
這種類型的文人,中國歷代有的是,認為詩賦小道,安邦定國才是大丈夫所為。我的看法,你要做政治家、教育家,你就去做,別做藝術家。拿破侖指揮軍隊,貝多芬指揮樂隊——這很好嘛。要拿破侖去指揮樂隊,貝多芬去指揮軍隊?
羅斯金人是好的,心是熱的,這是我的評論。他的觀點今已無人感興趣。
馬修·阿諾德(Matthew Arnold,1822-1888)。現在還常常提到他。詩人,以批評家傳世。他的可貴,是對產業革命以後的庸俗物質主義,大肆攻擊。我們目前所處的平民文化、商品極權,是他預見的社會。他是有遠見的。
羅斯金、卡萊爾,都可為了道德,藝術要靠邊。阿諾德不這樣。他從不標舉甚麼具體的道德方向,他知道藝術的道德是在底層。
我常說,道德力量是潛力,不是顯力。
福克納(William Faulkner)領諾貝爾獎時說:說到底,藝術的力量,是道德力量。大鼓掌。可他平時從來不說這些大道理。他書中不宣揚道德的。
道德在土中,滋養花果——藝術品是土面上的花果。道德力量愈隱愈好。一點點透出來。
哈代,陀思妥耶夫斯基,耐性多好!哪裏宣揚甚麼道德。
現代文學,我以為好的作品將道德隱得更深,更不做是非黑白的評斷。
他的行文,流利莊重,不明說,多做暗示。他認為文學是人生的批評。我有一句不願發表的話:
藝術家是分散的基督。
如果面對阿諾德,我就說給他聽。
沃爾特·佩特(Walter Pater,1839-1894)。他是個老俠客,樣子瀟灑,文章漂亮。唯美主義的旗手,是佩特。唯美主義的健將,都是他的學生,王爾德也在他旗下。
唯美主義起於英國,到法國後,法國人卻很自尊,不提佩特,其實法國那群精緻玲瓏的文人詩人,都受過佩特理論的影響。波德萊爾、魏爾倫、蘭波、馬拉美、瓦萊里、紀德,都從唯美開始,又能快步超越唯美主義,瀟灑極了。
佩特文體美麗。在西方,這種美麗的論文體是自佩特首創的。在中國,不稀奇。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,司空圖的《二十四詩品》,文字都美極,美得無懈可擊。這本應是文學的菜單,結果菜單比菜好吃。
他的《文藝復興》(The Renaissance)和《希臘研究》(Greek Studies),都寫得好極。他是文學上的雅痞。《想像的肖象》(Imaginary Portrait)是他寫的美好而不可及的傳奇。另有《享樂主義者馬利烏斯》(Marius the Epicurean)。
此公不能等閒視之。
英國歷史著作,麥考利(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,1800-1859)寫過《英國史》(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)和《彌爾頓論》(Essay on Milton)。
據說此二書受到現代人的重視,遠超過卡萊爾等人。他的文章無一頁沉悶。他表白的是多數人的見解,可是別人表白不清楚,在他卻是輕輕易易,通而不俗,文筆愉快。實際上,這種才能,正適合寫歷史。
托馬斯·赫胥黎(Thomas Henry Huxley,1825-1895)。這個人文章要看。很好很好。達爾文的繼承人、發揚者。他是生物學家,雜文、論文、講演,文學價值都很高,看似輕鬆,毫不在意,而又雄辯,旁徵博引。我很喜歡他的文筆,完全是文學家在那兒談科學。請各位留意,碰到赫胥黎的作品,別忘了一讀。
文章版權持有者: © 木心美術館。未經許可,不得擅自轉載使用。